
科学人生 | 我的洪堡学者生涯
【编者按】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8年初,教育部即发出《关于高等学校1978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意见》,决定将1977、1978两年招收研究生合并进行,统称为1978届研究生,当年全国招收了10708名研究生。千千万万名因文革而被耽误学业的莘莘学子,走进了考场,开始走上改变人生命运之路。今天历史已过去整整45年, 我们国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抚今忆昔,为了纪念这一对我国科学教育事业发展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本刊特组织当年参加研究生招考的考生,写下这段亲历的回忆,以飨读者。本文作者1964年大学毕业,因“文革”而以37岁“高龄”参加这次考试,并顺利于三年后成为文革后的首批硕士,继后很快成长为所在单位的学术骨干、德国洪堡学者,以及我国地震科学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我们今天回忆这段历史时,将更充满信心地坚持改革开放方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而努力奋斗。全文分上、下两部分分期发表,上半部分为在国内读研,下半部分为洪堡学者去德国访学。
我的洪堡学者生涯
张 流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学术界涌现了出国潮。国家需要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科技人员渴望学习到世界上的前沿知识和开阔眼界。
我读研究生期间,已有许多昔日的同学、同事走出了国门,也有些人陆续回国。他们都带回了一股新鲜气息。
研究生毕业后,我没有继续读博。当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尽快摆脱学生身份,在北京有一个稳定的家;同时寻找机会出国。
一天,我遇见朋友陈昌明和汪寿松(他们是中科院地质所叶连俊先生的学生和部下),知道陈获得了德国洪堡基金会研究奖学金的资助即将赴德。他们建议我也申请,还告诉了我申请的方式、途径。
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ftung (AvH),以德国著名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命名,已有近百年历史;宗旨是对外国年青的、有科学才能的科研人员,通过提供奖学金,给他们在德国进行科研工作的机会(参考:1987.10,联邦德国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介绍)。原则上它只接受40岁以下有博士学位的科研技术人员,当时中国情况特殊,科研人员年龄偏大,也没有博士学位可言,所以条件有所放宽。
我随后便开始了申请。成功的关键,一是你的科研经历和已经取得的成果,这体现了申请者的科研能力。除了我以前在矿物学方面的文章,主要便是我的研究生论文。工作量在翻译方面。二是寻找到一位德方东道教授同意接受,并拟好一份科研计划。此前不久,王绳祖同志刚刚从德国(当时的西德)回来。他作为马普学会的学者在波鸿(Bochum)鲁尔(Ruhr)大学F.鲁梅尔(Fritz Rummel)教授的高温高压岩石力学实验室工作了六个月,深得鲁梅尔教授好评。由于专业方向相同,鲁梅尔教授很痛快地同意了我去他那里工作,我拟定的研究计划也得到他的首肯。
洪堡基金会每年组织两次评审。1983年底,我接到基金会通知,我的申请获批。评审意见对我已有的科研成绩给出了好评,这是给予资助的理由。
1984年2月我前往德国。那时出国是一件很“隆重”的事,还带有几分“荣耀”。室主任马瑾(院士,已故),同事王绳祖、施良骐、崇秀兰、赵阿兴,同学周新华、陈文寄,以及妻子高平、儿子等都到机场送行。我的离开给妻子和孩子留下的困难完全被兴奋所掩盖,他们也傻乎乎地跟着高兴。
后来,我将在机场的照片给鲁梅尔教授看,他开玩笑说:像总统出访。
 机场送别(左起:周新华,陈文寄,烨儿,高平,赵阿兴,张流;右起:王绳祖,崇秀兰,施良骐,马瑾等)
机场送别(左起:周新华,陈文寄,烨儿,高平,赵阿兴,张流;右起:王绳祖,崇秀兰,施良骐,马瑾等)
1在不莱梅歌德学院
初到德国,首先要解决语言的问题。洪堡基金会可以提供四个月的德语学习机会,负责学习期间的各种费用。在多个德语学校中,我选择了不莱梅歌德学院。
歌德学院是专门给来德的外国人教德语的。学员来自世界各地,一期有二十余人。同期学员中有北京天文台的韩铁,他是得到马普学会资助去德的。
我们这期德语班,除了中国、美国和土耳其各有两人外,其他国家的都是一人,如日本、波兰、希腊、伊朗、阿根廷、巴基斯坦等,像是一个小小的联合国。
和我们打交道的是一位德国教员,讲课、练习……。最后有一次社会活动:两人一组,随便去一个单位(机关、学校、商场等)采访一位德国人,并请被访人为你的德语水平写一个评语。我的搭档是阿根廷愣小伙,一位养蜂者。他的德语比我好。我随他造访了一位大型超市经理。经理明白来意后,立即写了个条子给我们,把我们打发了。我们看不懂他写的是什么。回来后,有德语好的学员看后告诉我们:不友好。不过,我们完成了作业!
学习期间,歌德学院曾组织了一次去柏林的观光旅游。不知道为什么我和韩铁都没有去。只听回来的学员唧唧喳喳,说从西柏林去东柏林如何被检查……。
歌德学院还组织了一次去德国北部北海中一个小岛上的旅游。上岛以后,有免费的自行车可用。骑着自行车观光海景很是惬意。那时我们不懂这也是旅游的一种促销手段,一个劲夸德国人做事仔细周到。
不莱梅给我的印象是休闲、安逸、宜居。那里的一家中餐馆是我和韩铁经常光顾的。坐在那里,静下心来,仿佛就在我熟悉的扬州,只是服务员是位德国姑娘。一座不起眼的四个动物的铸像是这座城市的象征性地标——被称为四位音乐家的驴-狗-猫-公鸡。
2在鲁尔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高温高压实验室——正式的研究工作
鲁尔大学的中国人
从不莱梅坐火车到波鸿,鲁梅尔教授派他的学生Garbi来车站接我。我先到他的办公室,聊了一会。给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你用四个月学德语,这时间是浪费了。后来的生活表明,会几句德语还是给在德国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给交往带来了很多乐趣。我还用德语给基金会写过几封信,彼此都感到亲切。
数天后,鲁梅尔教授请我吃饭,并送我到我的公寓楼宿舍。同楼的中国人告诉我:你受到了特殊待遇。这里是学生住的地方,教授是不会来这里的。
公寓楼很大,“居民”以德国学生为主,外国人也很多。中国大陆来的多为同济大学的博士生和访问学者,还有好几位中国台湾来的学生和学者。
很快,我就接触到更多的在鲁尔大学里的中国人。他们分住在不同的宿舍楼里,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学生会。我们愉快地相处了一年零八个月的美好时光。现在还记得名字的有:储昭坦、陶庭树(来自江汉油田),张慎(女,学生会主席,哲学博士生),钱敏汝(女,后一届的学生会主席,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博士生),张申科(女,同济大学博士生)等。
有趣的是,在波鸿期间,学生会进行了一次改选。张慎继续任主席。当时我在野外,却被选进了“领导班子”,被年青了一回。
学生会曾组织过几次活动。记得有一次春节聚餐,所有成员都将自己的导师、东道教授及其家人请来。地点就在学校食堂。我们自己采购食品、自己烹饪。场面很是壮观、气氛热烈。鲁梅尔教授携夫人和儿子前来捧场,大学校长还前来致辞,钱敏汝担任翻译。

正式的研究工作
我开始熟悉德国同事和高温高压实验室。最初是参与Erik Rybacki的硕士论文的实验工作,借此以熟悉实验设备:一套液体介质三轴岩石力学实验装置,这和我们国内的设备能力相当,但控制系统和记录系统是计算机化的;一套气体介质三轴高温高压岩石力学实验装置,当时国内还没有。后者是我学习、工作的主要对象与手段。
同一组的成员都是鲁梅尔教授的研究生。除了E. Rybacki,还有Baumgartuna(研究方向是水压致裂),Muller(研究方向是Ⅱ型断裂),Hauizei ,Smoka,Garbi(唯一的女生,丈夫叫Edmon,由于他常来,所以也很熟)。
实验室有一个加工车间,三名工人。实验室加工任务不大,他们工作量很小。
E. Rybacki论文实验工作结束以后,气体介质三轴实验装置就由我使用了。
后来鲁梅尔教授看到美国断裂力学著名学者J. R. Rice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出裂纹扩展过程的断裂能的概念。对岩石(岩体)而言,断裂能为岩石破裂所需要的能量与摩擦滑动所需要的能量之差。如果这种破裂导致系统失稳,则就对应于地震,或模拟的地震。断裂能越大,系统积蓄的能量越大,破裂失稳导致的能量释放也大,对地震而言震级也就越大。鲁梅尔教授认为我们可以用实验方法测定岩石的断裂能,并研究其随温度、围压的变化规律。他建议我来做。由于我在研究生论文中已经完整的做过不同温度压力条件下花岗闪长岩的变形-破坏行为,对这一研究的结果也就有所预期。
岩石样品选择了相关实验常用的Westerly花岗岩。工作很顺利。留德快结束时,我将结果作了一个报告。这一结果的重要结论是:在地壳温压条件下,岩石的断裂能,先随深度的增加而增大,然后随深度的增加而减小。这一结果也构成了后来解释地壳多震层成因的重要基础。鲁梅尔教授高兴的说:“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在德期间,我曾参加过一次在慕尼黑大学举行的国际地球物理学术会议,并在一个分组会上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回国后又在一次国际会议(北京)上作了介绍,并于1989年发表在英国Phys. Chem.Earth杂志上。
在德期间,我还参加了一次野外工作。地点是德国和捷克边境的一个山区。那里有一个大型的花岗岩体。鲁梅尔教授团队在那里做水压致裂试验,目标是地热能的开发应用。但更直接的目的是检验他建立的水压致裂测量地应力(方向和大小)理论及他所设计的测量装置。他已为推广这一设备成立了一个公司。他们也已经多次做过野外工作,打了一些深井。我们这一次只是更接近该地区地应力状态的测量和地热能应用的技术问题。这次野外工作使我放开了眼界:实验室工作是和野外工作相通的。这为我后来有勇气接受油田应力场方面的课题建立了信心。
鲁尔大学规模很大,有多片建筑群,还配套有多个大型超市、书店、宿舍区等。我们实验室的那个片区主体是并列的四幢大楼。第一幢因为地基不好而被弃用。高温高压实验室在第二幢的一层。出了大楼便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植物园。工作间隙,我们会在植物园里转一转,放松心情,照照相。
穿过植物园便是一条碎石沟,雨季便是一条河,有桥到达对面的山区。那里有著名的鲁尔工业区的煤矿场。从那里可以绕到鲁梅尔教授放置野外设备的仓库。
一次我和Muller聊天,说到北京有几十所大学。他慢慢地摇摇头,认真的说:不可能。他是与鲁尔大学比较的。

3洪堡活动
洪堡基金会和西德政府给予洪堡学者有较高的礼遇。可有配偶和孩子陪同,基金会提供生活费。为了让高平有一段国外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我在德国的后期,她也去了德国一段时间。在知道她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后,鲁梅尔教授给她发出了邀请函,以便她能更方便地参与一些实验室工作。因此,她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去的。她常常到实验室参加我的实验,有时也到与她有关的实验室参观、座谈。
聚会
每届洪堡学者在首都波恩都有一次大型聚会,学者的配偶也可参加。聚会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游览莱茵河;参观波恩大学、听取秘书长报告、晚宴;参观总统府,由总统或议长接见。
与会人员有很好的宿食安排。活动的许多方面都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让我们感到异样,尤其是我们还刚刚走出国门。
一次大型晚宴,是在一个大厅里,大家自由聊天。服务员端着各种食品和饮料在大厅里穿梭,客人们自由拿取,边吃喝边聊天。基金会的秘书长(实际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也在其中。
有一次,会议请了一个有名的照相馆来人为来宾照相(也许是照相馆主动来做生意)。来宾的行动并不受干扰,摄影师只是抓拍。会议期间,洗出来的照片在会议室门口大厅展出。谁想要,当场付款拿走。我们选了几张,留下了几张,因为价格不菲(每张10马克)。我们回去不久,竟然收到了洪堡秘书处寄来的有我们影像的全部照片。
学习旅游
洪堡基金会还为每位成员及配偶安排一次为期一个月的学习旅游。之所以加上“学习”二字,是因为有许多参观项目是一般旅游看不到的。
我们在波恩集中。旅游的第一天准备去参观一个附近的煤矿,出发前有工作人员介绍。这个煤矿的特点是采出的煤通过传送带进入发电厂,输出的是电。
早餐后我感到有些腹胀,但由于是集体行动,又是与各国人员一起,我竟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老毛病,便和大家一起出发了。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在接近目的地时,我开始感到腹部疼痛。当大巴车下坡进入矿区时,我已经意识到不能坚持了,于是下车,并告诉司机一会返回时再捎我回去。高平陪我下了车,在路边等候。这次生病让我在波恩大学附属医院呆了一个月。当学习旅游结束时,我们也返回了波鸿,但却失去了一次了解德国的最好机会。
我是有健康保险的。一切开支,包括出租车费、饭费、医疗费,都由保险公司负担。
我住院期间,使馆的一位三秘来看过我(我回国后不久,他因病早逝,十分遗憾);波鸿鲁尔大学学生会派钱敏汝来波恩看我;在波恩大学学习的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孙永华大夫也来看我(他也是洪堡基金会学者)。
4回国
1986年2月下旬,我们回到了阔别两年的祖国。
洪堡的“告别礼”——不菲的捐赠
洪堡基金会对于完成在德工作的学者可以提供一定金额的、回国后相关研究所必需的仪器和书籍的资助。我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按照规定程序提交了申请,并全部得到满足。1987年10月捐赠物品送到。
获赠的仪器是鲁梅尔教授实验室正在使用的、惠普公司生产的一套仪器系统,包括计算机、函数发生器、示波器、万用表、信号放大器、数模转换器、绘图仪、打印机等数个部件和相关的软件系统。总价值达四万多马克。这套仪器极大地优化了我们的实验系统,减少了许多“土”气。
获赠的书籍有二十多本。一部分转赠给了所图书馆。一部分与我的研究紧密相关的留下了。我特别喜欢的是有关长石的一套英文巨著,因为里面的知识曾启发过我们破解了莱河矿的晶体结构。我曾希望它能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岩石变形过程中长石等的显微构造,但后来这方面的工作未能深入展开。
1988年2月,为这笔捐赠,西德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克里尔博士还来我所举行了一个交接仪式。我所副所长刘国栋出席并介绍了我所的基本情况。罗焕炎(我的导师,同时是所学位委员会主任)、王绳祖、洪汉净以及几位年青同事参加了仪式。我介绍了我们的工作情况。参赞先生参观了实验室,了解了仪器使用情况。
离开德国前,洪堡基金会还寄来了学者证书,并告诉我:作为洪堡的Research Fellow,以后来德国,只要出示它,使馆便会给签证。
告别德国同事
人们的许多习惯都是相通的。德国的同事在波鸿市中心的一个饭店聚集,送我们回国。当大家坐定后,Garbi和Baumgartuna讲话表达对我们的送行之意,并说明了用餐付费原则:各人自己点餐,自己付费;我和高平的餐费由他们二人付。
我和高平也举行了一个告别Party。我们自己包了包子,买了一些食品在实验室“宴请”大家,气氛很热烈。我对近两年的生活作了回顾,对鲁梅尔教授和所有德国同事的帮助表示了感谢。Erik Rybacki应鲁梅尔教授要求,并作为主要合作者讲了话。鲁梅尔教授特别向大家推荐了“中国包子”,他拿着最后一个包子嚷嚷:这是我的了!
临离开波鸿时,鲁梅尔教授和夫人都来送行。
中华洪堡学者协会
国内有一个中华洪堡学者协会联系回国的洪堡学者(包括台湾洪堡学者)。洪堡基金会和中华洪堡学者协会曾多次组织过聚会。地点多在北京,印象深刻的有1987、1997和2005的三次。也有一次在南京(1992),地点在东南大学。何泽慧、路甬祥、周光召、韦钰等都曾与会。会议有许多报告,内容是有关各自领域战略性的学术动态和思考。我的朋友钱敏汝曾有报告介绍了不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5二次赴德国
回国以后,王绳祖同志和我曾邀请F. 鲁梅尔教授和夫人来我所访问。我们请他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参观了我们的实验室并作了一次座谈。我们也都请了他们到家做客。那时我的家是一个建筑面积只有40余平米的小单元房:两个儿子住半间,一间为我和高平的卧室兼客厅。教授问我在哪里看书,我应付道:去办公室。
利用留下的洪堡提供的资助期,1992年我又去到鲁梅尔的实验室工作了四个月。这时何昌荣博士已从日本回国并来到我们实验室。他带来了实验系统应力-应变线性组合控制的新思路。这一方法的实现可以更好地研究岩石变形过程的峰后行为。当时我们实验室还不具备这种能力。于是向鲁梅尔教授提出了这方面的设想。他很感兴趣。我从设备重组做到样品实验。时间略显仓促。我离开时,我问是否将实验系统的附加部分拆除,他们反而表示留着。回国后,我们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一方法进行了讨论(1994,地震学报)。
6与德国建立长期合作交流关系
与Erik Rybacki的合作与交往,为实验室与德国长期合作建立了纽带。他博士毕业后去到德国波斯坦的地球科学研究中心(GFZ)工作,后来成了GFZ的高级研究员。
我的研究生肖晓辉、黄建国在九十年代中期去GFZ留学、工作,就在Rybacki课题组。我也曾受该中心Dresen教授邀请访问过GFZ,Rybacki负责具体接待。此后,周永胜到GFZ访问、工作,与Rybacki博士开展的合作研究,前后共有三次。他还两次邀请Rybacki来北京访问和交流。周永胜的研究生党嘉祥、牛露近期又访问GFZ,在Rybacki博士指导下开展高温高压岩石流变实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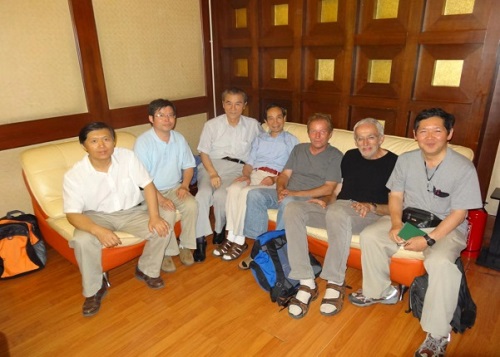 2012年7月Erik Rybacki 博士(右3)来访(左起:何昌荣、周永胜、王绳祖、张流;右起:日本学者Shimamoto 、Erik Rybacki的同事Janson)
2012年7月Erik Rybacki 博士(右3)来访(左起:何昌荣、周永胜、王绳祖、张流;右起:日本学者Shimamoto 、Erik Rybacki的同事Janson)
这些交往已经成了一种佳话。
如今数十年过去了,我们都已届耄耋之年。但回想起两年多的德国洪堡学者生活以及由此带来在各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与进步,应该衷心感谢国家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也得感谢这么多友好的德国同事,朋友,他们为中德友好交往以及两国的科技合作付出了巨大的热情和努力!
(本文作者系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贵公网安备 52011502000706号
贵公网安备 52011502000706号  贵公网安备 52011502002779号
贵公网安备 52011502002779号